微信扫一扫

姚家楼子小传(综合二)
商洛电视台副主编 本文作者姚书铭
锅片姚小识 · 之三
把《商山姚氏家谱·序》弄成大白话,我出了一身的汗。
我念中学时,还不兴高考,毕业了就回家种庄稼去了。后来的函授大学文凭,纯粹因为没有这一张纸就过不去许多的门槛,是看样学样混来的。我初弄文学时,一见没有标点符号的古书心里就虚,一见疙疙瘩瘩的之乎也者头皮就麻。是高中时期的语文老师贺,教给我一个秘诀——读古代文学,别顺着读,要倒着读。就是先从民末清初开始,沿着明元宋唐汉先往上爬,再从先秦开始,顺着汉唐宋元明清出溜下来。如此由近到远由远到近,反复出溜几遍,就行了。
我凭借自己反复出溜所打的微薄底子,才把手头的家谱序言掰掐成这个样子。我不敢肯定是否把笔者的笔意表达出来了,但序中所述“族兄凤展”四个字,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眼睛。
在我的故乡姚家楼,有两处较大的坟茔,一处在东湾,一处在邢家沟口——也就是我老屋背后五百米处。记得小时候,这老坟园里,有一岁一枯荣的芳草覆盖的墓堆,有和人一般高的长着苔斑的碑林,有胳膊粗的红藤缠绕的香花刺架。在那香花刺架上,除了香气袭人的白花,还挂着马蜂窝。捅马蜂窝对于一个孩子,那可是相当刺激的。然而,墓堆与墓碑以及刺架所形成的阴森森的渗气,使任何贼胆孩子,也不敢单个独行。
后来,到了文革时期,这坟园的碑刻作为四旧遗存被毁掉了。那一块块墓碑,有的被抬去修戏楼了,有的用于砌猪圈了,有的架在厕所池子上了。我亲眼看见那入厕的人,一边捉着裤腰站在碑子上撒尿,一边把脸迈向半人高的石头墙之外,跟墙外的行人打招呼:你吃了吗?我依稀记得,有的墓碑体积太大,抬石头的人,因肩膀的承重不够,就拿来八磅锤,抡过头顶砸将下去,墓碑就裂成一块一块的了。姚家坟茔里的碑林就这样荡然无存了,以至于后生们再去上坟的时候,也就寻不着老先人的坟头在哪达了。
再后来,我的父母去世了,也进了姚氏祖茔。为了使下我们的一代,不至于寻不着爷爷奶奶的坟头,我受兄弟姐妹之命回老家给父母立了一块墓碑。每次扫墓以后,我总忍不住要在坟园流浪一会。我还念那坟堆上的茵茵芳草,我怀念那香气袭人的香花刺架,我怀念那曾经的碑林。试想如果那碑林还活着,它拟或可以告诉祖上是怎样生的,怎样死的,怎样一代一代繁衍的,甚或还可以从碑文里找到锅片起源的线索。可怜那些会说话的石头,敌不过冷酷的八磅锤,现在连一个残块也不存了。八磅锤呀,你砸烂的岂是一块块墓碑,那分明是一部家族的绵绵的接力史啊!
又后来,社会成了经济型社会,钱的杠杆把人心世态撬得嘎嘎作响,形而上的追求日渐萎靡,形而下的物欲遍地横流,宗族之风气,也在不经意间悄然兴起了。族中的一个好事者,根据白胡子老者的记忆,用现代工厂生产的水泥,在老坟园里竖起一块墓碑。其复制的手艺,要多粗糙有多粗糙,碑上的用铁丝划拉出来的字,能称其为字就充其量了,和书法根本不沾边的。但有了这歪歪扭扭的文字,我这才看见,在我父母坟墓东边二十步处,那一堆起于顺治年间的累土,是“姚公凤展之墓”。我终于知道了,我的老先人,名字叫姚凤展。
手捧《商山姚氏家谱·序》,遥想祖茔的那一堆黄土。 锡胤公所说的“族兄姚凤展”,是不是那堆黄土里的我的先人姚凤展呢?
我口问心,心问口。
8时,姚兄怀亮敲门,应邀送来他从数部商志里摘录的姚辅、姚允元,姚锡胤、姚年晋、姚望祖的资料。以上数位,皆我祖上能人。怀亮兄一肚子古经,相谈甚欢。
11时06分,通过QQ,向zh-g老弟索要资料——“老弟好!前次得你提供的珍贵资料,不胜感激。昨晚一夜无眠,陷入两部姚氏家谱资料。反复阅读中得知,你前次提到的姚年晋,虽然不是姚家楼人,但也是一脉分支亲族,现在敬请你把手头《志稿》中相关文字,摘录发过来。年晋公的儿子叫姚望祖,《志稿》中有无记载?有劳兄弟你了,空口致谢!”
11时30分,zh-g老弟及时发来他正在整理出版的民国《续修商县志稿》资料——“年晋: 字丽明,号白山。康熙辛酉(1681)举人。少以文学知名,工诗善书。随曾祖湖广远安县署,后还商州。以州城迁屯满兵,移居东乡南谷中。会试不第,归就教职。著有《郡城山左》《汉南山中》《续山中》《周游》各集,并著《白山诗集》,颇多散佚。其子望祖搜遗,厘为六卷”。
zh-g老弟并发来年晋公诗8首以及注释两千多字。写介于文学与史料之间的文章,当然是资料拥有量多多益善,但随着资料的搜集,深感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我能挑起这副担子吗,诚惶诚恐!
锅片姚小识 · 之五
家谱者,一连串风干了的姓名。而那风干了的姓名背后,却是血性依然的生命和生命的延续。
姚家楼《姚氏族谱图》记载,锅片姚氏在第七世,有弟兄三个。老大叫姚宽,老二叫姚刚,还有一个叫姚聚。这和商州姚锡胤纂修的《商山姚氏家谱》所记,是一门一样的。所不同的,《商山姚氏家谱》一至于七世,只在序言里粗略说明,没有列出谱图。而姚家楼《姚氏族谱图》,一代一代谱图清晰,且有说明。姚聚的名下,就写着“无后”二字。
披阅姚家楼《姚氏族谱图》,不难看出,锅片姚氏,在第七世老大和老二身上,分为两股子了。
先说老大这一股子——宽生琇,琇生相,相有两个儿子,一个允元,一个允中。允元也有两个儿子,一个可仕,一个可任。姚可仕曾经做过太宁和苍溪两县的大拿,还做过新化州的一把手。姚可任的运气远不如他哥,活了八十多岁,一辈子只做过孩子王。好在那年头知识还没有贬值,教娃娃念书的人,也还吃得开。这教书匠的儿子,叫姚通方。通方的儿子,就是十三世的姚锡胤。
再说老二这一股子——刚的儿子叫姚玘,是个明经进士,学历还可以。玘的儿子叫姚辅,念书也还行。据王廷伊康熙四年《续修商志》卷五·明经栏目记载:“姚辅,玘子,蓬溪县令。致仕家居,琴樽自乐。”这个七品芝麻官,在案前是否压榨过他的子民?在案后是否收受过他人的黑脏?其靴子是不是常在背后踢人?其头上的顶戴是不是人血染红的?蓬溪地盘上有没有留下他长指甲扒下的一道道槽?不详。志书里记载的,这是一个想的开的老者,退休居家后,一没有官人放不下的臭架子,二没有退出官场以后的失落感,三没有老子曾经怎么怎么的想当初。他所有的,是调一调素琴,阅一阅闲书,喝两杯小酒。再有的,就是让小孙子叉开两条腿,伸手其间,笑笑地说:叫爷摸摸,本钱长了吗?他摸着孙子的本钱,皱纹脸上的老人斑里,十分敞亮地放飞着一个爷爷的自豪。我这样叙述,非凭空的杜撰,证据是姚家楼今天的爷爷们,不仅延续着摸孙子开裆裤的古风,而且依然把裆里的生命之根,叫做本钱!
见笑了,我的读者,可爱的你。
笑谈带住,敬请注意:这个姚辅,退休还家,家居何处?如果你以为他退居在商州城里,那就错了。请看,姚家楼的《姚氏族谱图》,有这样的记载:“姚辅,配党氏。字恭谷,号南雩。四川蓬溪县知县,致仕家居,琴樽自乐。一生品诣,详载商志。自此迁居姚家楼。”读者明白了吧——在明朝末年,这个有名有字有号的老汉,在退休以前就已经把他的家,从丹江上游的州城,搬迁到丹江中游山地来了。试问姚辅迁居的缘由,是兄弟睨于墙了?是邻里失于和了?是在州城和谁结孽了?是厌倦闹市的滚滚红尘了?是看中丹江中游的这一弯山地有旺人的风水了?这一系列的问号,都找不到揭秘的凭据,今天可以作为凭的,只有依照《姚氏族谱图》记载,确认姚家楼这一支脉的拓荒者,就是姚辅。
《续修商志》还记载:姚辅“多子孙”。
这在《姚氏族谱图》里,确有佐证的。姚辅的妻子姓党,名字叫啥,不详。过去的家谱,只写女人的姓而不具名,这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悲哀。聊可欣慰的,是这个无名的女人与姚辅通力合作,有了骄人的结果——四个儿子:秉夏、秉义、秉彝(群庠生员)、秉照——六个孙子:大雅、大韶、大咸、大谟、大勋、兴运——十一个重孙:建古、今古、维古、崇古……这一堆干巴巴的名字,你读起来是很费劲吧?那么笔者就直奔十三世的九个玄孙:凤鸣、凤展、凤翼、凤显……好了好了,为了不扫读者的阅读兴趣,后边的名字,还是从略好了。
看见老二凤展的名字,想必读者是不陌生的。他就是商州姚锡胤的族兄,也就是姚家楼祖茔里的殁于顺治年间的那个人。锡胤公曾经说:李自成手下部将袁宗第在商州屠城的时候,他老爷和他爷修撰的两部家谱还在,被“族兄凤展收藏姚家湾砦”。锡胤公所说的姚家湾,其实就是今天的姚家楼(关于地名的变迁,在后头当另立章回细说)。锡胤公所说的“砦”,是指姚家楼背后的小丘呢,还是指姚家楼对面的庵坡石窖呢?我对“砦”的解读,是依据词典,过去“砦”和现在的“寨”,音也同,意也通。姚家楼后头的小丘,今天还叫“小寨子”。在姚家楼一带,但凡称寨子山头,先前都有石头围墙和木头栏栅,族人一旦遭遇土匪了,就扶老携幼爬上寨子,壮汉们把守寨口,看见土匪来袭,就与石头和木头一起滚将下去,与土匪做着殊死的较量。现在的小寨子已经光秃秃的了,但它确实曾经是姚家楼人捍卫生命权的阵地。我的陈兄道久,对“砦”字却有另外地解读。这个老兄曾经做过商洛博物馆的掌门人,他一遇到“砦”,就确认那是一个天然的山洞。他的依据不是字典,而是凭自己数十年考古的经验。我倒觉得,实际的经验,往往比书生们掰掐的词典更靠得住。陈兄之说,在我的老家也有物证。姚家楼对面,丹江南岸的那座高坡就叫庵坡,庵坡上真的有许多天然的石洞。最大的洞口,在坡的上半身,进洞入底可听见丹江水响,能容纳数千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天然的石窖,曾经保住了姚家楼许多条性命。
姚公凤展,把祖上修撰的家谱,是珍藏于小寨子呢,还是秘藏于庵坡石窖呢?很难断定。原先的老谱,毁于火灾,有锡胤公的“祝融为祟”和遇孚公“祝融为灾”共同作证。并且,从二公的字缝里,还可以推测出这场火灾的时间段,大约在明末清初的五年间。那么,你或许要问:那一场所谓的“祝融为祟”,是族人的火烛之灾?是飞贼的纵火之灾?是国家军队的兵燹之灾?我手头的两部家谱,都闪烁其词,语焉不详,我也就不敢贸然结论了。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姚公凤展在火灾之后,并没有趴下!他率领自己姓刘的大老婆和姓张的小老婆以及儿孙们,该春耕时春耕,该夏播时夏播,到了秋天,用一把打了豁豁的镰刀,把地里成熟的庄稼收割回来,用石磨磨碎,叫大刘和小张煮熟了,给子孙们舀在碗里,吃!那是一个苍天不佑的大旱之年,干裂的土地里收成无多,他就刨出草根剥下树皮,叫大刘和小张拌和着五谷杂粮,给子孙弄成一种饭食,吃!即使草根和树皮也吃光了,他也毫不慌张地掮上被手掌磨细了木把的镢头,把后岭上一种白色的名叫观音的土,一筐一筐地挖抓回来,用那长着老茧的双手搓成面,吃!顽强的生命意识,在一种绝境中,被那个姚家老二化为极致!乱世中的姚公凤展,一辈子究竟受了多大的灾难,后人已经说不清了。后人能说清的是,丹江滩头的姚氏在任何灾难面前,都像他的始祖站在黄河滩头那样坚信——天无绝人之路!
锅片姚的薪火,就这样在凤展及其子孙的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上,得以相传,生生不息。
苦哉?凤展公说:不苦!酷哉?姚氏后人说:很酷!
速写于2011年12月7日凌晨5时30分
下节接述......


长按三秒识别关注
编辑 姚 波
世界姚氏宗亲联谊会

展示家族的辉煌历史 助于激励子孙继往开来
-

智慧花园
甘肃140㎡| 3室2厅 3800元 面议 -

风格宜居
湖北70㎡| 2室2厅 1600元 面议 -

润泽悦溪
黑龙江70㎡| 2室2厅 2800元 面议 -

润泽悦溪
黑龙江85㎡| 2室2厅 1300元 面议 -

诗景长安
福建86㎡| 2室2厅 1500元 面议 -

领秀慧谷
海南88㎡| 2室2厅 8000元 面议 -

国风上观
黑龙江86㎡| 2室2厅 5000元 面议 -

新龙公寓
黑龙江88㎡| 2室2厅 6500元 面议 -

国美第一城
黑龙江86㎡| 2室2厅 2800元 面议 -

诗景长安
河南86㎡| 2室2厅 5500元 面议 -

山水家园
黑龙江88㎡| 2室2厅 6000元 面议 -

千禧家园
福建88㎡| 2室2厅 6000元 面议
-

智慧花园
甘肃140㎡| 4室2厅 250万 面议 -

青年汇
河南70㎡| 2室2厅 120万 面议 -

新龙公寓
海南140㎡| 3室2厅 160万 面议 -

智慧花园
甘肃140㎡| 2室1厅 160万 面议 -

远洋山水
河南80㎡| 2室2厅 160万 面议 -

国风上观
河南160㎡| 4室2厅 170万 面议 -

风格宜居
湖北85㎡| 2室2厅 150万 面议 -

诗景长安
福建70㎡| 2室2厅 150万 面议 -

远洋山水
河南160㎡| 5室2厅 300万 面议 -

领秀慧谷
海南140㎡| 3室2厅 160万 面议 -

新龙公寓
海南140㎡| 4室2厅 115万 面议 -

风格宜居
湖北50㎡| 1室1厅 49万 面议
自定义html广告位
-
下一条:中华学术正脉的守望者姚奠中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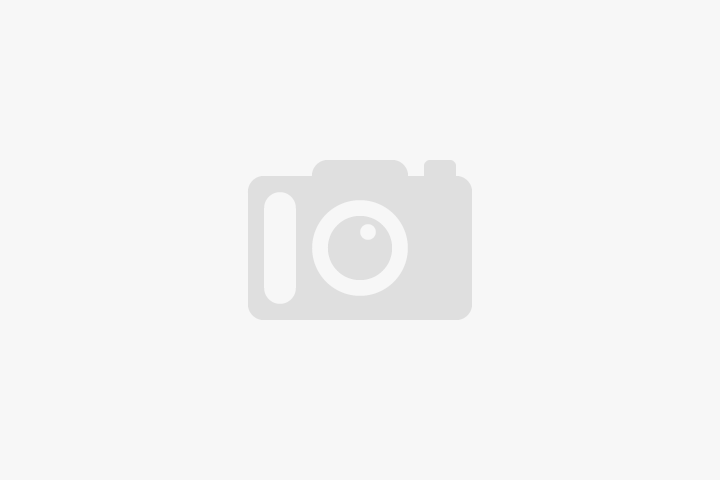
















 粤公网安备44030502001739
粤公网安备44030502001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