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扫一扫

历史小说:《千古帝舜》第四章
第四章 舜陶河滨
舜十五岁时,象和婐手也随着岁月的更替在长大。姚圩这一五口之家,已经明显地感到生活的压力。虽然壬女可以编织些筐子、箢箕之类换些粮食,虽然舜可以帮做一些农活和家务,但是一年难有几个圩落上门请瞽叟弹唱。再加上象又贪焚骄气,餐餐闹吃细粮食,吃鱼肉,婐手年幼,还需要人照看,壬女不得不改变维持生计的思路,敦促瞽叟由在家等人上门请弹唱改为送唱上门。瞽叟虽然眼瞎,但有心计,就把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练石补天,神农勇尝百草,共工怒触不周山,黄帝大战蚩尤等等编成词儿习练,还编排了些曲儿,什么“春祭”、“天问”等等。熟悉以后就由舜引路外出弹唱,竟然十分地受欢迎。每到一地,演唱完了,酋长或里正就赏给些粟、菽、稷甚至麻布、肉干。找准这条路,瞽叟有了用武之地,壬女少了生活压力,舜则乐得少了象和婐手的纠缠,少了壬女的喋喋不休。这样一来算是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开始的时候舜尝试着弹奏些简单曲谱,一曲下来竟然能得到一片赞叹,慢慢地,舜指法娴熟些的时候,瞽叟就干脆由舜管弹奏他自己只管说唱。父子二人配合得体,弹唱效果也更好了。
瞽叟虽然有音乐天赋,但是终归是没有跟过师傅,对乐理并不懂得多少,弹奏的曲谱套数不多,舜就有些不满足。爷俩在一起的时候,舜问这问那,常常弄得瞽叟很尴尬。瞽叟也悟到了舜的心思,决定带舜到龙泽去寻访自己学琴之初见识过的一个叫纪后的琴师。于是由舜领着边行边问。瞽叟少年时到过龙泽,是跟人乘竹伐子去的,这次走山路,路生,走了差不三天才到叫龙泽的大圩落。
老远就听见有琴声传来,虞舜凝神细听,越听越舒展。尽管父亲懂音乐,会弹奏,但是总觉得父亲的琴音之中缺少了点什么,现在听这琴音,听着听着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时而令人悲,时而令人喜,悲时想诉想哭,喜时想歌想舞,悲喜交夹之中,就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舜还是第一次感到音乐竟有如此大的魅力,他牵着父亲循着琴音寻找,到了一座草屋,伸头往门缝里一瞧,就见是一个白发老翁坐在院子里弹琴。舜就与父亲静静地坐在院落外门槛上听琴。
老翁发现门口有人,便立即停止弹唱,起身走到门边将门打开,十分礼貌地说道:“二位客人可到院里用茶。”,
舜连忙站起身,向老人施礼道:“对不起,打扰先生弹唱了。”
老翁发现舜背上背着一把琴,问舜道:“你们从那里来?来这里干什么?”
瞽叟说道:“我叫妫弦,年轻时候曾经在这个地方听过一个叫纪后的琴师弹琴,这次带儿子来,是送我儿子重华来向纪先生学琴的。”
老翁听后一笑,问道:“想这孩子就是重华了。我就是纪后, 琴弹得不好,令你见笑了,进屋来吧!”
舜牵引父亲进了院子,老翁又将父子俩让进屋里。舜见屋内书简满架,就知老翁是个高贤。便说道:“刚才我听纪先生弹琴,简直醉了。”
纪后十分谦虚地说:“过奖了,老夫莫过是自娱自乐而已。”
舜说道:“我父亲会一点五弦琴,我从小受感染,也爱琴,可我不懂音律,不知纪先生肯不肯收我这个徒弟?”
纪后说:“你找到我这儿来,多少证明你也会听琴。琴者,禁也,只有心性高雅之人,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琴师。”
舜说道:“小时候读书,听我老师也说过‘琴者,禁也’这话。先生是抚琴高手,德艺双馨,重华想拜先生为师学习琴法,”
纪后听舜说念过书,就问:“你老师是谁?”
舜答道:“我老师叫务成昭。”
纪后很惊奇:“你是务成昭的弟子?”
舜说:“是的,在他手里读过五年书。纪先生认识我的
老师?”
纪后摇摇头说:“听说过,但不认识。”
纪后年岁高了,已有几年没有外出弹琴,就带了几个徒
弟在家里教琴。舜登门求教,纪后见其天资聪明,心里早就喜欢上了舜,但还得看看舜的基础,叫舜弹了几曲后,就答应收舜为徒。鉴于实际情况,觉得不宜将舜当做关门弟子
就出主意要瞽叟在龙泽住一段时间,对外的弹唱可以照旧进行,一来解决食宿费用,二来可以积累些粮食带回家里,早晚或者闲时就让舜学琴。
当下,舜向纪后行了拜师大礼。纪后起身到壁柜中,取出一圈书简来交给舜说:“先好好看看书简,不懂的地方就问我。”
打开一看,书简是部琴书,里面画着许多琴的式样,各处部位都注明了名称,加了详细注解,书简后面附有很多
曲谱。舜不识谱,纪后当下就教会了舜识谱方法。
按照纪后的办法,爷俩每天外出弹唱回来,舜就上纪后处学琴。
纪后琴弹得好,而且深通乐理,还会制作乐器。纪后跟舜说:我们的先祖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了习练乐律。无论是被称为人皇的伏羲,还是神龙氏炎帝,还是轩辕黄帝,都对音乐有特别的感悟和喜好。伏羲“听八风而授民,举六佐以自策”,常常亲自一边弹拔琴瑟一边歌唱,还叫一些身边的人以箫、管伴和,每次音乐起处,百鸟和鸣。神农氏炎帝“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轩辕皇帝则命令乐师伶伦创制“六律”、“六吕”。轩辕黄帝以后的近祖颛顼帝“召朱襄后裔善音律者夷生,会八风之音,为圭水之曲。合钟鼓,作基英之乐,鸟兽万物,莫不应合”。纵观历史,上下数千年,音乐源远流长。
舜对纪后这番话,有些听得懂,有些听不懂,但已经悟得了一个道理:人类的先祖无论是伏羲、神农或是黄帝、颛顼,没有一个不喜爱音律的。都擅长于用音乐谐合人与人,人与自然,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纪后又详细地向舜说了五弦琴的制作过程。纪后说,五弦琴和音乐的发明都源于劳动。当年炎帝部落为发展农业,曾经大面积开垦荒地,荆棘劈斩完了,只剩了一棵高大挺拔的梧桐。炎帝叫人找来麻绳,先在梧桐树上拴一根绳子,用五个人拉,梧桐纹丝不动;炎帝就叫拴两根绳子用十个人去拉,梧桐仍然纹丝不动;当拴到五根绳子用二十五人拉时,梧桐仍然只微动而不倒。炎帝发现了弊端,原来二十五个人用力不协调。炎帝就叫邢天去指挥。邢天急中生智,就用宫、商、角、徵、羽作口令,每哼一个音,就用一次力。第一遍哼过,五根绳子被绷得紧紧的,颤抖着发出悦耳的弦音;第二遍哼过,梧桐树开始抖动,出现和谐的共鸣;等到哼过三遍以后,梧桐树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随着轰鸣停止,绳断了,梧桐倒了,树干齐崭崭地折断,里面是一个空洞,长三尺六寸五分,恰好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吻合,炎帝认为这是天意,就将中空的桐木精心加工,齐边刮削、打磨,制作出了琴身。再用五根精制的丝用黄蜡抹过作了琴弦,然后再组装好,并按照“宫、商、角、徵、羽”调试好五音。炎帝又叫邢天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炎帝亲自操琴演奏《下谋》之乐,唱起《丰年之咏》,于是百鸟和鸣,白鹿击蹄,人们都和着粗犷奔放的旋律,踏着有力的脚跳起了舞。
舜听了纪后的一番话论,茅塞顿开,知道了音乐源于生产生活的道理,也悟到音乐的教化力的神奇,他下决心要把五弦琴习练到出神入化程度。
不知不觉在龙泽呆了数月。舜天资聪明,加上基础较好,通过纪后点拔,舜懂得了很多音律乐理知识,弹琴的技巧提高了不少。出外时日久了,瞽叟与舜商量着该回姚圩了,于是舜别过师傅纪后,背上弹唱换得的粟与稷,用马杆牵引着背着琴的瞽叟,踏上回姚圩之路。
正是春夏之交,沿途鸟语花香,父子俩心情特别舒畅。舜心里温习着纪后师父的教诲,构想着制作神龙琴的方法。他打算回去后自己动手制作一把琴,往后再外出弹唱,就可以与爷或分或合变些花样吸引更多的听众。正沉思间,身后一声响亮,舜牵引瞽叟的马杆不翼而飞。回头看时,父亲已滑出小道,仰面跌落坡下。舜慌忙梭下坡扶起父亲,连问摔伤没有?瞽叟在舜的搀扶下慢慢站起,伸伸腿,弯弯腰,甩甩胳膊,腰有些隐隐作疼,他怕舜急心,只说没事。舜小心翼翼地把父亲扶上小道。瞽叟忽地记起了背在背后的五弦琴,手弯到背后一摸索失声大叫:“琴呢?琴呢?”舜一惊乍,忙拿眼睛往坡下搜索。五弦琴还在坡下,他急忙再次梭下坡。“爷,琴头摔碎了”。舜几乎用哭腔告诉父亲。瞽叟急不可耐地叫“快拿过来看看”,舜爬上坡,双手将琴递给父亲。瞽叟双手哆嗦着,颤颤地抚摸着断了的琴弦,泪水从失明的眼里流了出来。喃喃地说:“老天要绝我,要打我的饭碗啊!”舜见不得爷那悲怆的样子,眼泪也在眼眶里打着滚,安慰说:“爷,回去我们再造一个”。瞽叟说:“容易吗?这是我眼睛好的时候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做好的啊!”舜心里啄磨,爷曾经造过琴,虫古师父又讲过造琴的方法,自己为什么就不能造出一把更好的琴来呢?于是安慰父亲道:“碎是碎了,天不早了,回家再说吧!”瞽叟不再说什么,父子俩商定先不把琴摔破之事告诉壬女。瞽叟牵着马杆,强忍腰疼,跟着舜忐忐忑忑重新上路。
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走了几十里山路,瞽叟的腰疼痛难忍,回到家倒头便睡。壬女听说瞽叟闪了腰,将舜骂得体无完肤,说什么老大不小了,爷老子都领不好,把爷老子眼睛克瞎了还嫌不够,还想克掉他的老命;说瞽叟不如跌死好些,跌死了少个负担。摔坏了琴,瞽叟本就心情不好,壬女火上拨油,不由得又凭添了几分忧伤,在床上一躺就是半个月。这天,附近有人来请弹唱,瞽叟只好告诉壬女琴摔坏了。送上门的粮食飞了,想起家里的粮食又已经所剩无几,壬女心里无明火不觉添了三分。恰恰这时候,舜手里抱着破琴进了屋。打自从龙泽归来,舜无时无刻不在琢磨如何制作出一架琴来。下午放牛,他偷偷把琴带到放牛坪,按照纪后老师介绍的制琴方法,对照着爷制的琴琢磨如何从选材、造型、长短、大小等方面改进,造出一把好琴来以解爷之忧。此时,舜怀抱着破琴本想回家依旧藏好,没想到正与怒容满面的壬女面对。壬女瞧见舜,瞧见舜手里抱着的破琴,怒火中烧,一把从正处于惊愕中的舜手里夺过琴来重重地摔在地上。“呼啦”一声,琴碎成了数瓣。壬女凶相毕露,又接二连三用脚狠劲地跺,边跺边骂。脚脚都似乎跺在瞽叟与舜的心上。瞽叟从床上溜下地,摸索着一把拉住壬女,口里叫着“唉哟,我的娘哪,我求求你别这样,别这样!”舜则呆了、傻了。琴碎了,爷眼睛看不见,连个比照的模子都没有,琴还怎么制呢!壬女狠狠地推开瞽叟,又用脚把碎片扫得满地都是,边骂着边进了里房。舜悲愤痛惜,强忍泪水,弯腰拾捡碎片,没发觉刚才后母夺琴时衣绊被扯落,娘留给的那块粗玉在他胸前甩动他也全然不知晓。躲在一旁看热闹的象,突地跑过来,一把抢落了挂在舜胸前的粗玉转身就跑。这块粗玉是娘临终留下的,舜视为性命般珍惜,平时从来就不示于人前,现在被象抢了,舜完全失却了理智,箭一般追上几步夺玉。象死命不给,舜就用蛮力夺。象“嗷嗷”尖喊,倒在地下打滚,哭着叫着:“哥哥打死人啦!哥哥打死人啦!”壬女从里间出来,从象手里拿过玉,口里说着:“什么臭东西呢,婊子给的呢。”壬女把玉甩在地上就欲用脚跺。舜可以忍辱负重,但是绝对容忍不得母亲握登的形象受到亵渎。顿然,舜如同角斗红了眼的牛犊般扑向前,把壬女四脚八岔推倒在地。壬女后脑勺重重地撞在墙上即刻起了大包。舜转身拾起自己的粗玉。壬女骂着:“你这白眼狼崽,王八羔子,老娘喂大了你,你竟敢打老娘”。边骂边弹起身,顺手摸过倚在墙边的一根大棒。舜见势撒腿跑出了门。壬女追出门,高声骂着,早不见了舜的影子。壬女屋前屋后屋里屋外寻找,边找边骂。左邻右舍的人探出头看看,又缩了回去,人们素知壬女厉害,虽然同情舜,但是不敢捅马蜂窝。
舜深知撞了大祸,径直跑到娘的坟边,给娘下过跪,磕过头,便嘤嘤地哭泣。哭了好一阵子,就给娘的坟头拨草。天已经黑了很久,家是绝对不敢再回了,就窝在娘坟边,把拨落的草盖在身上睡觉。舜已经打定了主意去陶台。他曾经跟爷到过陶台的,这是个有名的古圩,在黄河河滨,盛产陶器出名。姚圩的陶叔就在陶台制陶。上次随爷到陶台,陶叔曾趁空带舜到制陶和烧窑的地方看过的。陶叔还开过玩笑叫舜跟他学徒算了。舜想着想着就睡着了。醒来时天已亮了。舜偷偷地溜回到陶叔家敲门,把要去陶台找陶叔的话告诉了陶叔的娘,并托姚奶奶传信告诉爷,免得爷急心。
舜这年才十六岁。十六岁的舜从太阳出山走到太阳落岭,整整走了一天才到陶台。他找到了陶叔。后来通过陶叔介绍并担保,舜最初时被安置在一个窑上作杂务。
按窑上规矩,掌管一座窑的头叫窑师,负责制作的叫模匠,模匠再下就是杂务。杂务算最低层,专干重活脏活琐碎活。专门负责看火候的叫司炉,另配有两个烧火的火工,白天黑夜轮流着烧窑。
舜先时帮砍柴薪,跟着另几个窑的杂务,走进林木葳蕤的樵林,把树枝劈削下来,挑到窑附近晒干、码垛、备用。这一干就是半年多。每天上山、砍柴、回窑,周而复始,十分单调。陶叔不知从哪里给弄了一个叫做陶哨的乐器给舜。那陶哨椭园形,侧有五个小孔。舜开始吹不响,久而久之就吹响了,觉得声音很好听,就慢慢摸索吹法,开始的时候吹得不成腔,不成调,几天以后就吹得非常悦耳,过了一段时间竟然能够吹奏复杂的曲调了。一天晚饭后,舜独自爬上陶台古圩后的一座小山吹陶哨玩。悠扬悦耳的哨声引来了一个叫虞邱的窑师。虞邱有个特长,很擅长用陶泥捏制小物件,一团陶泥在手,三下两下就可以捏出一头牛,黄牛是黄牛,水牛是水牛,大牛是大牛,小牛是小牛,神态各异。也捏些陶哨、陶鼓、陶钹、男男女女的小泥人,小马、小狗、小猫……无论什么都拿捏得活灵活现烧制出来后的小动物活灵活现,陶哨、陶笛音调好听,音阶准确。陶台古圩的圩头便特地为虞邱开个小窑,专门烧小品。陶台烧制陶缸、陶罐、陶钵、陶碗一类的窑数十口,烧制小品的窑唯有虞邱掌管的一口。这样,虞邱就成了一个特殊人材,很受尊重。方才听到舜吹的陶哨声不但古朴浑厚悠扬动听,而且是从未听过的新曲,
虞邱循声找到沉醉在陶哨声中的舜,通过攀谈后知道了舜的来历,就要舜吹一曲给他听。舜就吹奏了一曲。虞邱询问是什么曲子?舜告知这是颂扬轩辕皇帝的《云门大卷》。虞邱问为什么叫《云门大卷》?舜告诉说:黄帝初受命的时候有象征祥瑞的彩色景云预兆,所以黄帝就以云任命官员,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所以颂扬黄帝的这个曲谱就叫《云门大卷》。虞邱很惊讶。古曲是纪后老师作为范曲教给舜的,本来用五弦琴弹奏,却被舜作为了习练陶哨的曲子。虞邱听完吹奏,目瞪口呆老半天。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在陶台还藏匿着这样一个能通今晓古的少年郎。于是说:“从明天起,你就别打柴了,到我窑上跟我干吧。”
舜到了虞邱窑上。开始,他只是做质量把关的事。即是一件一件的小品地检查,看东西经过炉里高温烧后变形没变刑,陶哨吹得响吹不响,颜色好、形状好、音色正的就算合格。小件用小窑烧制。所谓小窑,是相对大窑而言。大窑烧大件,窑高一丈余,十余人方能合围,其中大窑中的龙窑,不但大,而且长,一头低,一头高,火从低处起,热力往高处传。小窑规模就小多了。窑高莫过三四尺,两人可以合围,装窑烧窑并不须多用人,一、二个就够。一窑货出来检查质量是尽管舜做得兢兢业业,认认真真,但也无须多少时间,闲下来时舜就帮助做些合泥、踩泥、砸饼、弄坯之类的活,慢慢就学着捏制、装窑、看火。第一次学看火,小品出窑后成品莫过四成,舜很不好意思。虞邱告诉说,是火候不到。从窑门观看陶坯底层的变化,倘使陶坯一红就堵火太早,底层陶坯从发红到堵窑还须烧半天。按照虞邱告诉的办法,舜试烧了第二窑。这次他加大了火力,时间也烧得长一些,可是一出窑,废的仍然很多,而且炸裂了不少。虞邱告诉说,开始上火不要太猛,猛了陶坯非炸不可。同时出窑时要慢慢地打开窑门,先上后下,窑门敞开太快也容易炸。舜把虞邱的教诲谨记在心里,用在烧制中,每一出窑,他都把上、中、下层面烧出来的陶件打破数件仔细观察,看火力到功不到功,过火没过火,发现陶件表面颜色与中心不一样时,就分析原因,分析来分析去,就发觉仅仅表面火力到功还不行,这并不就意味着烧透了,于是在烧下一窑的时候就修正烧火时间,设法不出现这种现象。他冥思苦想,千方百计地寻找少出陶器废品,使烧件结实耐用的方法,下决心要做出质量上纯的陶器。
舜在小窑上一干就是两年多,不知不觉已经快十八岁了。虞邱为人厚道,正直公允,心里一直很喜欢舜的聪明勤快谦恭上进好动脑子。眼看着舜跟了自己两年,虞邱不允许自己因为喜欢而误了舜的前程,他到处夸舜是个好料子,最终把舜推荐到了大窑当模匠。舜用半年的时间学会了大件陶器的盘筑制坯。又用半年的时间学会了使用转车。所谓盘筑制坯就是用泥条从底到壁再到口盘成各种陶器粗坯子,然后用泥桨胶合好,再过细整形成全器。所谓转车是一个圆形平台,台面置于轴上,一个车把连接着轴,用左手将轴在竖直面上一转动,平台就转动。工作时,在平台和轴上装陶摸,陶模里砸满泥巴,然后随台面绕轴旋转,再用削刀把泥胚胎体削制成薄薄的、各式各样的陶件。学会了盘筑和转车,就有了资格做司炉。
烧制陶器是一个劳动强度很大的过程。大窑制一窑货,光制作泥件就需要两个多月,装窑五天,烧火三天三晚,再算上合泥、踩泥、弄柴等等工日,出一窑陶器真是很不容易。装窑烧窑是一窑陶器成败的关键。因此,陶台人把窑看得十分神圣,每年都要举行祭窑仪式。祭祀那天绝对不准杀生,不准说“破”、“碎”、“垮”、“塌”一类字眼,以免坏了彩头。祀礼上备了“三牲”,童男、舞女、乐队,庄重非常。倘若有了谁在祭窑当天犯了忌讳,处理是非常严的,轻则遭棒杖,重则沉河杀头。另外,对装窑的过程和烧制的方法和程序也十分严格,先祖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办法被奉为唯一,是绝对不许违背或者更改的,谁违背或者更改,造成出窑不顺,就要受到鞭笞,棒杖甚至取头祭窑。
舜当上大窑司炉后很快就把祖传的装窑、烧窑、出窑章法规矩烂熟于心。但是,好动脑子的舜心里有好多好多的问题:为什么一年四季变更夏季热死人冬来冷死人,自然温差那么大,而烧火的时间长短总是三天三晚一成不变呢?为什么烧成的陶器总有那么多裂的、破的、变了形的呢,为什么每出一窑,废品都那么多,然而尽管废品成堆,个个窑师却都习以为常呢?有不有办法既缩短烧火时间节约柴薪又提高陶器合格率呢?有不有办法能使烧出的陶器既结实又美观呢?舜逢人就求教,暗暗地思索琢磨,偷偷做各种试验。当摸索出经验后,就叫虞邱先在小窑试烧。虞邱按舜的办法烧制出的小品陶器废品少了,漂亮美观多了。可是舜在大窑试验时却撞了大祸,烧出了一窑废品。圩头与窑头兴师问罪,将舜捆绑结实,吊在刑棚,召集陶台全圩人看棒杖示众。
当虞邱得到消息的时候,他绝不相信舜琢磨出的方法会出废品,心想必有缘由,就急急地赶到刑棚打听。窑头说舜擅自改动烧窑方法,在窑上开了孔,而且不按祖传办法先封了窑顶再烧火,而是烧了半天火才封窑顶,这就使窑破了气。并且告诉虞邱这违规的事在火烧了一天后就被另一掌作厉止发觉了。厉止虽然偷偷把孔阻死了,可已经晚了。虞邱又问了一些情况,心里明白了事情的症结所在,就向圩头跟窑头求情,说了舜很多好处。最后求圩头让舜再烧一窑试试,倘再出废品,愿意跟舜一起共同承受更厉害的惩罚。虞邱为人正直,资格很老,平时在圩头心里就有位置。圩头就给了一个人情,大声而严肃地向众人宣布:“倘舜再出废品,将与他的师傅虞邱一块受五刑责罚。”
舜开始并不知晓开的孔被厉止阻死的情况。这次舜再不敢掉以轻心,舜申明,除了他的师傅,除了要两人帮烧火,其它什么人也不准上窑干扰。圩头许诺。舜亲自装窑,为了使一些特薄的陶件不至于被压变了刑,他别出心裁地把一些特薄的陶件用陶泥做成的厚薄适当的匣子装好封死再上窑。装好后,又上窑顶仔仔细细检查了烟囱,同样地在窑后侧把自己曾经钻开,后又被厉止封死的左右两个孔打开。这一次,舜特别地加搓了两根半尺多长的泥条,把两根泥条先装进陶管再插进孔里。起先,窑仍然没有封顶。做好了一切以后,舜才点了火。舜亲自烧火,开始火烧不很大,烧了约两个时辰,窑顶冒出的烟没有了湿气,舜才叫帮手上大火,自己在一旁观察。大火一上,敞开的窑顶先时冒出红色火舌。烧了约四个时辰,窑顶的红色火舌。开始夹杂有了绿焰,舜即上窑把窑顶封了,把两个插泥条的孔也用稀泥抹了缝。当烧到两天两夜后,舜从窑门往里看,底层的陶件红通通了。他立马爬上窑,分别把泥条从左右侧壁取出观察,发现右侧壁的泥条红得还差些火候,就又烧了两个时辰。舜再上窑顶取出左右侧壁泥条查看,这时泥条均已红得耀眼,舜即叫两个帮手协同封了窑口和烟囱。
一天一夜以后,舜先把烟囱打开散热,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再打开侧面两个孔,又过了一段时间才打开窑顶和窑口,并且口子先时开得很小,再慢慢开大。
第二天天亮,要出窑了。天一大早,圩头早早地就到了。俄刻,窑边就围满了人,窑师、模匠、司炉来了不少,都知道舜这窑陶器烧得成功与否非同小可,事关两个人的名声和安危。来的人都怀着各种心态,关心舜与虞邱的希望成功,平时与二人有些不快或心胸狭隘、有忌妒心理的希望出点忿子。圩头与窑头则静静地等待着结果再作结论。窑头先派了两人负责出窑,又选派了一个窑师检查质量。出窑的每把一件陶器递到负责检查的窑师手里,窑师都一一仔细看过,同时用手里的小石子轻轻叩几下。听那声音很清脆。再看那陶器外表光鲜亮丽,窑师忍不住连声赞叹:“好成色!好品相!”圩头看那陶器件件锃明瓦亮,用手指弹之铮铮有声,心里也暗自称奇。一窑陶器全部出窑后,竟然只碎裂了十来件,而且其中不乏出窑时失手碰破的。再看那破碎的陶器片,表里成色相同,结实程度远远胜过旧办法烧制的陶器。最后,出窑的把几个匣子弄出来了,全场的人表情漠然,都不知晓舜耍的是什么把戏。当舜亲自动手把匣子接口处小小心心凿开开后,人们愕然了,匣里封着的薄薄的酒樽祭器一类平时极容易压碎弄扁的陶件,一件件完好无损,锃黑发亮,窑四周人们欢呼声雷动。圩头和窑头惊愕得嘴巴张开老大。有几个平日很有些拿大的窑师朝舜伸出大母指夸赞:“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哟!”虞邱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舜挣出欢呼的人群,跑向虞邱,司徒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舜烧陶“器不苦窳”的名声广为传播。舜独创的的烧陶方法广为流传。十八岁的舜被制陶人尊崇之至。


长按三秒识别关注
编辑 姚 波
世界姚氏宗亲联谊会

展示家族的辉煌历史 助于激励子孙继往开来
-

智慧花园
甘肃140㎡| 3室2厅 3800元 面议 -

风格宜居
湖北70㎡| 2室2厅 1600元 面议 -

润泽悦溪
黑龙江70㎡| 2室2厅 2800元 面议 -

润泽悦溪
黑龙江85㎡| 2室2厅 1300元 面议 -

诗景长安
福建86㎡| 2室2厅 1500元 面议 -

领秀慧谷
海南88㎡| 2室2厅 8000元 面议 -

国风上观
黑龙江86㎡| 2室2厅 5000元 面议 -

新龙公寓
黑龙江88㎡| 2室2厅 6500元 面议 -

国美第一城
黑龙江86㎡| 2室2厅 2800元 面议 -

诗景长安
河南86㎡| 2室2厅 5500元 面议 -

山水家园
黑龙江88㎡| 2室2厅 6000元 面议 -

千禧家园
福建88㎡| 2室2厅 6000元 面议
-

智慧花园
甘肃140㎡| 4室2厅 250万 面议 -

青年汇
河南70㎡| 2室2厅 120万 面议 -

新龙公寓
海南140㎡| 3室2厅 160万 面议 -

智慧花园
甘肃140㎡| 2室1厅 160万 面议 -

远洋山水
河南80㎡| 2室2厅 160万 面议 -

国风上观
河南160㎡| 4室2厅 170万 面议 -

风格宜居
湖北85㎡| 2室2厅 150万 面议 -

诗景长安
福建70㎡| 2室2厅 150万 面议 -

远洋山水
河南160㎡| 5室2厅 300万 面议 -

领秀慧谷
海南140㎡| 3室2厅 160万 面议 -

新龙公寓
海南140㎡| 4室2厅 115万 面议 -

风格宜居
湖北50㎡| 1室1厅 49万 面议
自定义html广告位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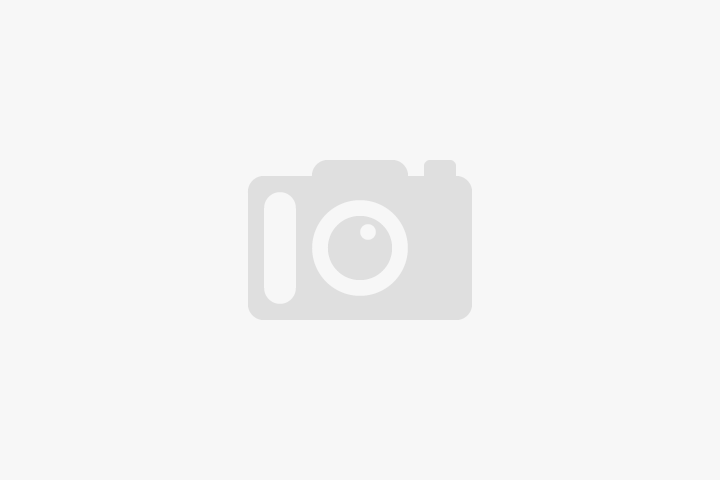
















 粤公网安备44030502001739
粤公网安备44030502001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