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扫一扫

寻访京郊山西移民村落(节选)
寻访京郊山西移民村落(节选 )
http://www.sxgov.cn/ 黄河新闻网
一串地名揭开移民传奇
北京市大兴区有条河叫凤河,相传是供帝后妃子垂钓的河,所以叫凤河。凤河长约50里,在大兴流经5个乡,两岸星罗棋布数十个村庄,沿河边一路走去,能看到村子里成排的平房,以及连接各村并不太宽却很平整的道路,完全是北方普通农村的样子,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
奇怪的是村名。
从青云店镇的石州营村开始,包括长子营镇,、采育镇,一直到凤河营镇,细心的人会发现很多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庄,几乎小二十个,诸如孝义营、霍州营、解州营、潞城营、黎城营、沁水营等等,不一而足,而不以山西地名命名单以“营”说的村庄,更是不可胜数,当地有两句俗谚,一是说,“五台八庙七十二连营”,另一句是说,“山西多少县,大兴多少营”,稍显夸张,但也部分符合事实。
地名的命名素来不会随意,总有其地理或历史的原因,这么多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庄,说和山西没有关系,那是说不通的。当地人都说,他们都是明朝山西移民的后代,先祖迁徙至此,为解乡思,为志故土,就将所居之地以家乡名字命名。“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民谚在当地也是广为人知,妇孺老幼也能说得出来。长子营镇白庙村80岁老人贾朝恩更言之凿凿,先祖是“永乐癸未年”从山西前来的。
贾朝恩老人的话,他祖祖辈辈也都是这么说的,考诸正史,也有佐证。
永乐是明成祖朱棣的年号,癸未年是永乐元年,按公元纪年则为1403年。这一年最重要的事,自然是永乐改元——明成祖朱棣经过四年鏖战,取得了史称“靖难之役”的胜利,终于篡逆了他侄子的江山——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盛世的开端。
不过,当时的人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帝国。四年的战火,打断了明初以来的休养生息过程,中原、华北、华东又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人烟”的悲惨景象,尤其是北京地区,作为朱棣的龙兴之地,所以也是靖难之役开始南京建文政权重点打击的区域,兵燹之害尤其严重。据有些记载表明,相较于元末,北京地区人口下降了一半还多。
永乐元年,朱棣将北平改为北京,称“行在”(皇帝行銮驻跸的所在),亦称顺天府,与应天府南京规格对等,就此拉开了迁都的序幕。
迁都北京,是朱棣即位后第一件大事,从他个人来讲,他受封燕王、就藩北京二十多年,对这儿感情深厚,且势力根深蒂固,远非南京可比;从国家的层面来说,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部边疆,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后,能够方便有效地调配整个国家的军事和经济资源,保障帝国的安全。而迁都的第一步,就是用移民以充实北京。
在改元前一年,即洪武三十五年(也是建文四年,朱棣为抹煞建文帝的影响,将建文在位的四年都沿用洪武年号,变相地让朱元璋多活了四年),朱棣命令户部:
遣官核实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使置牛具子种,五年后征其税。
村落档案
屯留营
该村位于采育西0.3公里,东依凤河,北临104国道。明朝初年,由山西屯留县移民至此而建村,当时的6户人家为纪念祖籍,取名屯留营。
下黎城营
该村位于采育西0.5公里,东临凤河。明朝初年,山西黎城县移民至此而建村。原由大圈子营和小圈子营两个自然村合成,为纪念祖籍黎城县,并区别于北面的上黎城营,故取名下黎城营。
南、北辛店
该村位于采育东4公里,明朝初年自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由于此地是北京至天津大道的必经之处,往来客商、行人食宿者很多,当地开店的较多,故以得名。明朝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就叫辛店镇,并已有集市。
(1)解放前辛店分成南辛店和北辛店。
(2)1976年南辛店又分成南辛店一队和南辛店二队;
1983年公社改乡后,改称南辛店一村和南辛店二村。
考虑到行政运作,洪武三十五年发布命令,永乐元年移民正式开始是合理的,也和那位贾朝恩老人源自祖辈的说法暗合,明永乐初年山西移民北京的史实确凿无疑。
史家考证,永乐年间,大规模的移民共有八次,且出发地大多在山西,目的地多在北京,移民数55万,有效地恢复了靖难之后战火波及地区的社会、经济,为定都北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以大兴区而言,移民“立营58”,使得大兴的户口人数增长了6倍有余,从一万多人,增加到七万多人。
六百多年后,这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移民事件,在正史中只有片言只语可寻,在当地,哪可能见到六百年前的房屋,也难觅纪录家族历史的宗谱,让它终于成为一个久远的传奇,只有那些传承六百年的地名才顽强地承载着移民的记忆。
大兴区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庄,青云店镇有石州营村、孝义营村、霍州营村、解州营村,采育镇有屯留营村、东潞州村、大同营村、山西营村、下黎城营村、铜佛寺村(原名高平营村),长子营镇有赵县营村、沁水营村、(上、下)长子营村、河津营村、上黎城村、北蒲洲营村、潞城营(一、二、三、四村)、永和庄村、南蒲洲营村、和顺场村。另外,周营村原名叫绛州营村。
顺义区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庄,赵全营镇(为“赵县营”转音)有东、西绛州营村,忻州营、稷山营、红铜营村(与“洪洞”音同),高丽营镇有河津营村和夏县营村。
不仅如此,那些并非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庄,根据方志记载,移民村落也非常多。如《大兴县志》就记载:
于家务,明初从山西省移民成村,相传村内曾建有姜太公庙,庙里竖一根鱼竿,以祝福村民年年有余、幸福,后谐音为于务。清光绪年间名于家务。
祁各庄,据传明初从山西省迁来王、张、马、周、邢、刘六户,从山东迁来毕姓一户,因七户在此定居,取名七家庄,后谐音改为祁各庄。
大皮营,明永乐间从山西移民建村,因村中有一皮匠手艺超群,远近闻名,故得名大皮匠村,后简称大皮营。
哱罗庄,明代建村,村中有柳编作坊,所产笸箩远近闻名,故村名笸箩庄。因字体繁琐,后改名哱罗庄。
诸葛营,明初山西移民至此形成村落。曾名曹庄子,后改朱家营。清末,以村人许半仙智谋过人,遂将村名改为诸葛营。
……
如此计算下来,大兴区共526个自然村,其中110个自然村由山西移民组建。
亦可证明,永乐年间的数次移民,也并非仅仅是普通的民户移民,如史籍所载,来源亦有罪人,“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其余有罪皆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也有身怀技术的人,“从山西之平阳、泽、潞等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今天的采育镇,仍以葡萄等瓜果蔬菜知名,历史的遗风余绪犹存。
自然,六百多年过去,如今山西移民后裔早就成为纯粹的北京人,满口的京韵京腔,但中国人素来就有追根溯源的文化传统,在很多人心里,山西并不是离自己很远的一个不太发达的省份,更不是地图上一个枯燥的名字,而依然是,老家。
本报记者 李遇
请看下文
曾经,沁水营村在搞基建平整土地的时候,从地下挖出许多骨灰坛来——那些移民的先祖,宁肯违背自古以来的土葬习俗,也要留存一丝再回山西老家落叶归根的希望。到了现代,他们村的三任支书,也踏上了到山西的寻亲之路,只是,时隔六百年,他们还有可能和故乡的宗亲联系上吗?故乡的人,对这些远亲,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三任支书回晋寻祖溯源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每当人们哼唱起这首民谣,不禁想起那场著名的明代大移民。这场发生在明朝洪武至永乐年间的移民大迁徙,几乎席卷大半个山西。这些地区的迁民临行前,大部分人在洪洞大槐树下,办理迁移手续,领取户部颁发的迁移堪合,叙旧告别,然后挥泪各奔去处。
六百年前,交通不便,小小沟壑亦是天堑,荒了人烟,绝了音信,即便是五百公里之外的京师,对于留在山西老家的人来说,也算得上天涯那头。六百年后,有这么些当年移民的后裔,回到山西老家寻根觅祖,想要连接上那条曾被官府生硬割断的血缘链条。这拨回乡寻祖的移民后裔来自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沁水营村,带领寻祖考察团的是先后三任村支书——张贺才、冯学文、郭振会,他们心中锁定的老家是山西晋城的沁水县。
山西有沁水县北京有个沁水营
本报报道组一行抵达的沁水营村,在北京市东南郊,距六环城区25公里,离大兴区政府所在地黄村东偏南21.5公里,南触凤河傍水而居。村域南北长约3000米,东西宽约千米,村域面积2.59平方公里。在接待本报报道组时,沁水营村当地人“自报家门”说,祖上生活的地方就在现今的山西晋城的沁水县一带,当时由沁水县迁移来的移民共16姓18户,现已知的有郑、刘、张、韩、赵、豆、吕、冯、任、崔、李、涉、郭、康等14姓16户移民到凤河北岸建村,为不忘祖居故里,特以原籍沁水县命名,村名为沁水营。
《沁水县志》记载,沁水县明时隶冀宁道,清代属泽州府。明初,朝廷颁布移民屯田令,半奖励半强迫开垦拓荒,在明初的18次移民中,沁水县向北京地区进行过4次移民。
而大兴当地的地方志上说,“据《明太宗实录》卷三十一记载“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自山西太原、平阳、泽、辽、汾、沁民万户实北平。”又根据《明太宗实录》其他卷及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等文献推断,沁水营建村的时间应为建文四年(1402年)至永乐五年(1407年)之间,其中,永乐二年(1404年)和永乐五年(1407年)建村的可能性最大。”
两段地方志所记载的内容,隐隐约约存在某种关联。字间所指,似乎可以穿越历史,看到同一宗族的亲人被朝廷强令分割迁移的画面。可惜两段地方志文字记载的部分语焉不详,总缺乏点实实在在的铁打证据。
编纂村志,重回故里
虽然历史久远,很多事情无法具体说清,但沁水营村人心里对先祖根脉的认定却不会减退,他们曾两度专程赴山西考察历史,探访故里,希望能找到一些证明自己“身世”的证据。
在沁水营村村支部会议室,曾任沁水营村村支书,后任长子营镇副调研员的冯学文先生,对本报记者描述起“回家寻祖”的前后经过。
沁水营村人首次“回家寻祖”是在2009年8月,但早在两年前,村干部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2008年,沁水营村村支书郭振会正式提议,把沁水营村的来龙去脉“整理清楚”,最好能形成正式的文字。冯学文先生是大学本科学历,在历任村干部里属高学历,他有随时整理手头资料的习惯,这么多年手头积攒了大约10万字的文字档案,冯先生说:“也就是把以前豆腐账一样的散碎资料,整理成相对有价值的线索。不过,写出来的文稿我感觉并不严谨,很多地方没有印证。”
2009年6月,大兴区史志办负责人和沁水营村党支部及编写成员再度商讨沁水营村志编写规划,查看村里的部分设施。史志办负责人建议分两步体现沁水营的发展历程,一是将村子发展搞成展室,以实物展现;二是整理、编修村志,并在2009年8月,与沁水营村修志人员一起前往山西历时9天寻根溯源,挖掘历史资料,真正了解了明朝政府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缘由和先人在沁水营这块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的艰辛。
山西沁水人的后裔,在先祖背井离乡举家迁移的六百年后,终于重履故土。张贺才、冯学文、郭振会等5人考察组先后在太原晋祠、晋城市地方志办公室、洪洞县大槐树祭祖园、洪洞县史志办研究了解,当然,考察地的重中之重,还是老家沁水县。
难觅历史证据,收获浓浓亲情
沁水营村村支部的会议室墙上挂着一幅巨幅山水国画图,看不出具体是哪儿的风景,记者开玩笑地问冯学文先生,“是老家山西的风景吗?”冯先生很认真地摇摇头。其实,会议室的布置真的看不出有什么山西的痕迹,记者仔细寻找,有点落空了,也许这种落空的感觉,就和沁水营村考察组想在山西找到移民证据时的感受一样。
冯学文先生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和山西沁水县志办的同志们见面时的情景。他和张贺才、郭振会这三任村支书刚一进沁水县志办的工作室,自我介绍身份后,对方先是大感意外,但立刻表露出只有老乡相见时特有的浓浓亲情,“他们(沁水县志办)知道有明初移民的历史,但并不知道具体迁移到哪里,更不知道在北京还有我们这样的沁水后裔。
“说实话,这次有些失望,寄希望能找到山西方面翔实的文字资料,甚至还指望能看到某本沁水县的传世家谱,明确记载着永乐哪年哪月哪村,谁家的小子迁徙到京城了,这样我们的后裔身份就对接上了,但结果一无所获。”双方相互留下联络方式,约好日后加强联系,互通有无多多走动。山西沁水县赠以“北京亲人”的沁水县志相关内容,也被《沁水营村志》大量直接引用。这种穿越时空的血缘之亲,似乎也算一定程度的重续。
转过一年,张贺才、冯学文、郭振会带队再回山西考察寻祖,这次回乡队伍的规模更大,共有70人。虽说结果和上次差不多,具体线索寥寥无几,但考察团收获了满满的老家情谊,不少地方邀请他们品尝山西美食,体验山西文化,沁水营村的人的感觉是陌生且熟悉,至今全村仍偏爱面食的饮食习惯,让他们在山西没有半点别扭。在晋城市区,他们的大巴找不到高速路口,随便找人问路,热情善良的晋城小伙先是指路示意,后来干脆开车带路专门把他们送到高速口。沁水营村考察团回到北京后,一致认为山西老家人实在、朴实、热情。
虽说没有达到最理想的寻祖目标,但“北京沁水”和“山西沁水”方面共商典籍,还是有些确实的史籍收获。冯学文说,“我们村的移民先祖应该是明初山西大移民的第一拨人,证据就是沁水营村名的命名——明朝官府允许第一代移民以家乡的县名来命名迁移后的聚居村名,后来官府意识到这有可能滋生思乡之情,继而抵抗迁徙令,就禁止再用原来地名命名新村名了。”
沁水县欢迎移民后裔常回家
从京返晋,记者联系到了晋城沁水县志办主任侯晋林,向他询问有无可能找到有关移民北京的文献记载,最好是能完成北京那边村里想搞懂谁家的哪个姓,究竟源自沁水哪个村的愿望。
侯晋林主任坦诚地连道“很难,很难”,他向记者解释为什么北京沁水那边知道自己的祖籍,而沁水县却不识“北京亲人”的原因:“我们的《县志》内容,主要根据县里保留的清朝康熙、嘉庆、光绪年间的三版旧志而编纂,这三版旧志对明初移民并未明确记载,像‘沁水营’三字更是只字未提,所以真不知道还有这些北京的后裔。”另外,在沁水县范围内找记载了明初移民的家谱,技术难度上比较大,他们也曾在全县寻找过上了年头的家谱,但发现这方面的历史资料非常稀缺。
貌似寻找家谱机会渺茫,但也绝非毫无可能,侯晋林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前些年,同是明朝移民后裔的河南某村族人携带家谱而来,寻到沁水县嘉峰镇李庄,在当地找到与其家谱记载内容,严丝合缝高度吻合的村人,与当地家谱相对照,二者记载的方位、距离和迁移时间较吻合,两地人家本是一家。
说到“北京亲人”,侯晋林说当时一看到沁水二字就亲近得不行,那种亲人团聚的感觉直到现在记忆犹新。侯晋林说,沁水县有打算在合适的时候做个回访,看看那边是什么样子,沁水县也真心希望和欢迎北京的移民后裔随时回家住住,看看。
记者临回晋前,冯学文说了这么一句——希望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先祖,通过明明白白的考证,把沁水营的昨天留给沁水营的明天。其实,这句话,对我们山西这边,亦同一理。
本报记者 刘巍
村落档案
大黑垡
该村位于采育东4.5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因移民至此正值黑夜,故取名大黑垡。
半壁店
该村位于采育东南5.5公里,明朝初年建村。当年此地有两座庙宇,定以两庙相对线为准建村,但要在相对线的一侧盖房,形成半部建村,故名半壁店。
倪家村
该村位于采育东南6.5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县移民至此而建村。因当时倪姓为村中之首,故取名倪家村。
祁各庄
据传明初从山西省迁来王、张、马、周、邢、刘六户,从山东迁来毕姓一户,因七户在此定居,取名七家村,后谐音改为祁各庄。
请看下文
沁水营村的三位村支书回到了六百年前的故乡,感受到了家乡人的温暖和亲近,但有关明初移民的详细官方记载和民间家谱却没有找到。他们说:我们是山西人的后裔,可谁知道?有证据吗?
槐亦是怀满载移民寄托
大兴区的采育镇到青云店镇有一条路,叫青采路。冬日里,路两侧30里老槐静默安然,透过光秃秃的枝丫把灰蒙蒙的天勾勒成一幅写意的图画,落日余晖的任意涂抹,让这条路显得严肃而深沉。当地人说,这些槐树守在青采路上的时间并不久远,但它们的存在是在延续一份600年无法割舍的乡情,是一种故乡的象征。
在大兴,在那些用山西地名命名的村落里,在山西移民后代生活的村里,村民们说,这里曾有一棵与山西同根同源的古槐,是明代移民时从山西带来的。
全国乃至全世界,从来没有哪一棵树有洪洞大槐树那样高的知名度,它让全球两亿多大槐树移民后裔牵肠挂肚、魂牵梦萦,它被崇拜为根、祖、家的图腾,成为家山故土、灵魂所寄的象征。
洪洞老槐树植于洪洞县唐代重建的广济寺中,这棵老槐相传为汉代所植。当年洪洞作为转移移民的聚集地,人们守在槐树下不愿离去,扯着老槐树的枝丫,抱着老槐树的枝干,嚎啕不放。无情的刀剑斩断了槐树的枝丫,人们紧握着手中的槐树枝,被驱赶着远离了自己的故土。
“槐”者,“怀”也
这份灼人心尖的思乡情被寄托在静默不语的槐树上。
大兴县《沁水营村志》记载:解放初时沁水营有槐树二十余棵,其中四五百年树龄的槐树有五六棵,皆为汉槐。也就是说,这里种植的那几株老槐都与洪洞广济寺的槐树同根同源。
古槐,不语,却用年轮一圈一圈记录下与故乡的联系。
民谣,口口相传,以另一种方式来告诉一代又一代的人——我们来自哪里。
“房前种上大槐树,不忘洪洞众先祖。村村槐树连成片,证明同根又同源。”这心酸又无奈的歌谣,被顽强地一代一代传唱。当年移民们一步一回头地离开故土时,手中的槐树枝不仅见证了离乡一幕,也同远离的人们一样在异乡扎下了新的根基,长成了一棵参天古树。
山西移民的许多村落,房前屋后,村头地边,都种植有槐树。《大兴县志》和《采育镇志》中都有关于古槐的记载:
凤河营乡张各庄村,两棵树龄300年的国槐;
红星区亦庄乡小羊坊村,明代清泉庙遗址500年国槐;
北营村一棵国槐,
大黑垡一棵国槐,
红星区东磁各庄,300年国槐一棵,北京市一级保护林木;
采育镇广佛寺村一棵国槐,
屯留营村一棵国槐,
北辛店村一棵国槐,为北京市二级保护林木。
按照这些记载,元宵节,我们去探访了当地一些还遗存的古槐。
来到屯留营,一眼就看到沿着村牌楼进去的水泥路尽头有一棵大槐树,树径一米以上,用铁栏杆精心地保护起来,外面挂着牌子,醒目的红字写着:保护古树,人人有责。村民申丙歧今年已过60岁,他告诉我们,不用说他,村里90多岁的老人说打记事起,这棵树就这么粗了。
距离屯留不远是北营,村庄已被推平,村民都搬迁到了采育镇新建好的小区内,如今只剩一片被蓝色挡板围住的空地,等待新的建设。挡板一侧有个缺口,缺口处,一棵槐树坚强挺立,同样挂着被保护的标识。它没有被围着,人们可以走近,三个人都抱不拢。猛地发现,槐树下有明显祭拜过的痕迹:插在地里的几把香头簇新,烧过纸的灰烬还没有被吹散,三颗新鲜的橘子散落在树根下。
沁水营村志里有这样一段话:槐树在新土地上生根长叶了,移民们在新地方住下了,安心了。槐树开花结果了,移民们也在新地方繁衍子孙了。他们把栽植的槐树当做故乡的象征,当做祖先的象征,对它爱护和尊敬。逢年过节,人们面对槐树念故土,想亲人,寄一切情感于槐树。有人烧香,献上供品,朝槐树叩拜。家里有什么难事或灾病也面对槐树,祈求祖先保佑。这种做法沿袭成习。
槐树在移民心中有另一番异于旁人的情感寄托,在移民后裔的村落中,纵然古槐或是干枯而死,或是砍伐而亡,都不会形神俱灭,这里的人们会再次栽种下新的槐树,那份情结生生不息。
北营、屯留营的古槐不知几百年,青采路上的国槐不足百年,沁水营新种的国槐不足十年……可无论这些槐树有多少年的历史,它们都承载同一个意象,有着同一个故事。
“乡”者,“想”矣
故乡,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都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当我们远离家乡,当岁月磨掉诸多痕迹,当我们忍不住追问,我来自哪里时,探寻的脚步便会踏上归途。在一点一滴早已淡漠的痕迹中寻找蛛丝马迹的联系。
沁水营的乡情村史陈列馆中,那些已经变成展品的农具中,有一片巴掌大的铁片,两寸多长,一寸多宽的长方形,一条长边卷着一条粗麻绳结成的绳套。使用这个铁片时,把大拇指之外的四指穿过麻绳套,握住这个铁片,便可以使用了,主要是用于割谷穗或是在不便使用镰刀的地方收割高粱。沁水营的前任书记冯学文告诉我们,这种农具在当地叫爪镰。2009年8月,他们回山西沁水县找寻移民记录时,曾在沁水县看到过同样的农具,仍然有人在用。
山西很多地方把收割谷子叫掐谷,谷子是很精细的籽实,经不起大手大脚地摆弄,不能用大镰刀割,要用爪镰一棵一棵地掐下谷穗来。除了在收割谷子时会用爪镰外,给核桃蜕皮也要靠爪镰。核桃是沁水县重要的经济林木。刚入秋的时候,在白露之前,核桃就开始成熟了。成熟的核桃带着青涩的皮打回来,就需要爪镰给它们去青皮。左手用指尖轻捏着青皮核桃,右手除了大拇指,其余四指套在爪镰的带里,在核桃上一转圈划过,干干净净新新鲜鲜的核桃就出来了。
长子营镇白庙村村民贾朝恩说,村子里曾种过谷子,他所知道的刀把齐、大毛刺、龙爪鹰等谷子品种就是过去从山西带来的。长子营镇的很多村子里有一句农谚:“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落荞麦。”三伏天之后种荞麦的种植习惯也与山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年在仓促而被迫的状况下远离山西,人们能带走的只是有限的生活必需品。贾朝恩说,过去村里有一种大木轮子的小车,推起来吱吱呀呀的,俗称“叫蚂蚱”,当年的移民就有人推着这种车,车上或者肩上会搭一个“捎马子”,北京叫“褡裢”。“捎马子”这种叫法,在晋商云集的晋中地区非常普遍,走西口的商人们,以及当年的驼队人人都有一个“捎马子”,用来装随身的物品。
有家就需要有各种家当来过日子,惜物又节俭的山西人总会小心地保护好自家的那点家当。可是岁月长河,600多年足以让很多东西消失于无形中,尤其是杯盘碗盏这些易碎品,被驱赶离家的人又能带走几件这样的易碎品啊,可是一路吃喝总是需要碗碟不是?在大兴的民间收藏家那里,我们有幸看到了几件从村里收藏来的物件,白色的瓷碗、瓷碟,线条流畅,一只盘子中刻画出一朵莲,另一个盘子中则是几条水草和两只圆润的鸭。轻轻敲击时,碗碟发出有如石磬的清音。碗碟是用覆烧的技法烧制的,覆烧技法是历史上定州窑烧制的主要工艺。山西历史上大同、怀仁、平定、阳泉、介休、榆次、霍州等地皆有烧制瓷器的窑口,烧制的瓷器皆属于定州窑系。
我们不是文物鉴定专家,不能对这些碗碟的历史做出评断。但在碗的底部有一个黑色的卍字图形,一个王字,一个寿字;碟子的底部则是刻出的“官”字。过去在山西一些大户家,家用物品上往往会打上自己家族的印记,也许只有与这些碗碟同源的人才能明白这些字代表的涵义吧。
更多精彩内容请至原文阅读
长按三秒识别关注
编辑 姚 波
世界姚氏宗亲联谊会
-

智慧花园
甘肃140㎡| 3室2厅 3800元 面议 -

风格宜居
湖北70㎡| 2室2厅 1600元 面议 -

润泽悦溪
黑龙江70㎡| 2室2厅 2800元 面议 -

润泽悦溪
黑龙江85㎡| 2室2厅 1300元 面议 -

诗景长安
福建86㎡| 2室2厅 1500元 面议 -

领秀慧谷
海南88㎡| 2室2厅 8000元 面议 -

国风上观
黑龙江86㎡| 2室2厅 5000元 面议 -

新龙公寓
黑龙江88㎡| 2室2厅 6500元 面议 -

国美第一城
黑龙江86㎡| 2室2厅 2800元 面议 -

诗景长安
河南86㎡| 2室2厅 5500元 面议 -

山水家园
黑龙江88㎡| 2室2厅 6000元 面议 -

千禧家园
福建88㎡| 2室2厅 6000元 面议
-

智慧花园
甘肃140㎡| 4室2厅 250万 面议 -

青年汇
河南70㎡| 2室2厅 120万 面议 -

新龙公寓
海南140㎡| 3室2厅 160万 面议 -

智慧花园
甘肃140㎡| 2室1厅 160万 面议 -

远洋山水
河南80㎡| 2室2厅 160万 面议 -

国风上观
河南160㎡| 4室2厅 170万 面议 -

风格宜居
湖北85㎡| 2室2厅 150万 面议 -

诗景长安
福建70㎡| 2室2厅 150万 面议 -

远洋山水
河南160㎡| 5室2厅 300万 面议 -

领秀慧谷
海南140㎡| 3室2厅 160万 面议 -

新龙公寓
海南140㎡| 4室2厅 115万 面议 -

风格宜居
湖北50㎡| 1室1厅 49万 面议
自定义html广告位
-
下一条:老兵姚国太:历史仿佛就在“昨天”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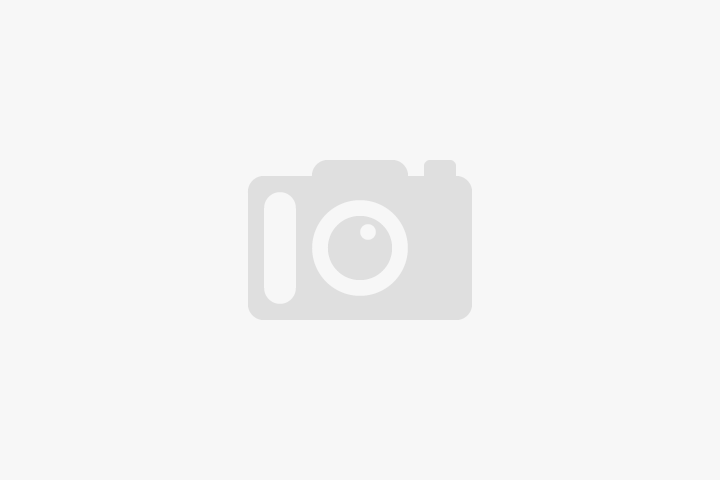
















 粤公网安备44030502001739
粤公网安备44030502001739